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钱教授对我来说,总是感到有亲和力。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6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我正在负责筹备家乡浦江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我于1995年7月份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张主任恰好是浦江同乡,他非常热情,主动邀请钱理群教授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我,就因这很偶然的因素,我结识了钱理群教授。96年3月,我一到北大旁听中文系的课程时,首选了钱理群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教授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在北大6年,我也似乎成了一名“钱理群谜”,凡是有钱理群的课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去听讲,有钱教授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记得我刚开始听钱教授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教授签名留念。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钱教授在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钱教授提了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的。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此认真的回答。我与钱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经常见到钱教授,他总是提着一个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个布袋),总是那么忙忙碌碌,碰面了我都会郑重地道一声“钱教授,你好”,他也是那么一脸如来佛的笑脸向你点点头,算是给你最善意的回敬了。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会,也没忘了请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钱教授,有一个大大的秃了顶的大脑袋,穿着也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钱教授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己见地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在北大,他除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加,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来北大旁听、进修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我就不知一次在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教授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也无不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象是久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我的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他与我谈起他曾得到钱教授无私的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便冒昧请钱教授担保办理借书证,钱教授知道陈君是为了求知请他帮忙,便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帮助他,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教授的热心肠一直温暖了陈君很久很久。(现在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只要有身份证和交每天2元的费用,就可办理一个临时阅览证后,便可在图书馆的阅览室自由阅读报刊图书了。)陈君还告诉过我,在他身无分文的困难时期,曾向钱教授求助,钱教授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百元钱,并说这点钱先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陈君还说到他的北大饭卡也是钱教授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着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啊。我还听说过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教授打电话,自称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教授能够帮助他。钱教授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及时送到那位旁听生手中。我曾听说过浙江诸暨的一位乡镇普通干部辞职来北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课程后回到原单位时,领导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现,否则要辞退他。这位北大旁听生冒昧写信请钱教授帮忙,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写了这位同学在北大的表现良好的信寄给当地政府,为那位旁听生救了急。去年3月,我在北大发起创办网上《北大边缘人报》,并着手编著《精神寻梦在北大--北大边缘人的故事》。最近我已写信给他,希望钱教授作序,相信钱教授会有十分精彩的文章寄给我们的,我和所有得到过他帮助的北大边缘人都在真诚期待着。

电梯维保员述职报告怎么写
听钱教授的课,每位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钱教授的一位学生郑勇曾在文章中生动描述过他的讲课时写到“钱理群的选修课在北大出名地受欢迎。限定中文系的课,外系的学生会来旁听;限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也会来抢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转移到大教室,因为人多,有时一学期要换几次教室。39岁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上过老钱课的人,都会对他独一无二的讲课风格留下极深的印象。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轮的鲁迅、周作人、曹禹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摘下,一会戴上,一会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跟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这里要补充的是,钱教授的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他提倡学生提问,不论在课前还是课后,他都会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钱教授的课,还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如他在讲“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时,上学期由他主讲,下学期就改由一名学生主讲、学生讨论与导师点评的新式教学,先由学生主动报名,再与导师选定主题,由学生备课拿出教案,最后由学生上讲台上课,此对于提高学生的治学热情和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学相长啊。前来听钱教授的课,既有北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的青年教师和教授,也有来北大进修的访问学者、进修生和考研者,更有不少纯粹为了求知而不为文凭来北大游学的作家、学者、诗人和追求政治的旁听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辍学的中学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学子。钱教授的课,有非凡的魔力,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被他那磁铁般的讲课所深深吸引。
公司律师的工作标准
我在北大的6年,通过听北大张岱年、季羡林、吴小如、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孙玉石等名教授的课程或学术讲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学的一些路径。其中钱理群教授与陈平原教授对我治学影响尤深。他们两位不愧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巨擘,我也常常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叹为观止,甚至感到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困惑。但我在听他们的课程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发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欣赏他们,主要是欣赏他们从事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从他们身上,我渐渐读懂了北大,正如钱教授对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 “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导师钱理群教授的指引下,定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道路来报答北大的恩师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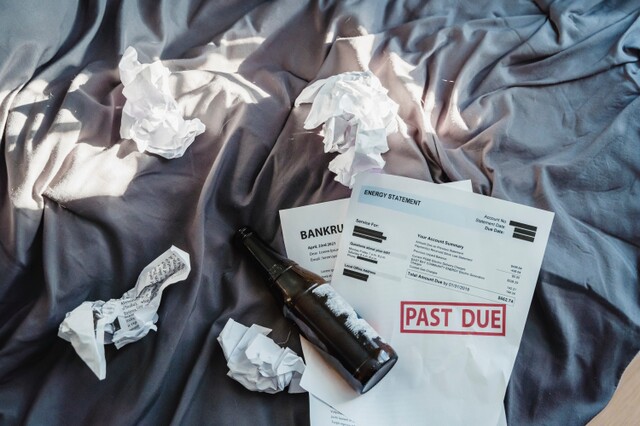







 隐患整改通知书_
隐患整改通知书_ 花茶的优美句子_
花茶的优美句子_ 经典心情不好的签
经典心情不好的签 部编版三年级下小
部编版三年级下小 unit5综合测试卷a
unit5综合测试卷a 猴年机关单位春联
猴年机关单位春联 网店促销活动策划
网店促销活动策划 债权转让公告格式
债权转让公告格式 幼儿园开学通知美
幼儿园开学通知美 高中生迟到检讨书
高中生迟到检讨书 破坏公共设施的处
破坏公共设施的处 员工录用通知书of
员工录用通知书of 3.8妇女节简报_3.
3.8妇女节简报_3.